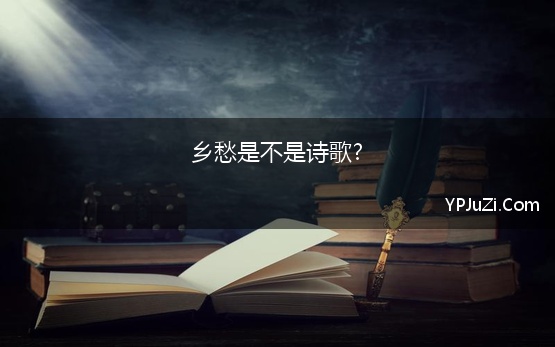现代诗歌与当代诗歌的关系 艾华林:《当代·诗歌》的现代性表达与欲说还休的语言艺术

《当代·诗歌》的现代性表达与欲说还休的语言艺术
文/艾华林
在《当代·诗歌》(试刊号二)的卷首语里,商震的叙述从“我”妈妈家不远处的一条据说是连通着京杭大运河的人工小河谈起。当他看见盛开的莲花和青翠的莲叶,便联想到小河连通着京杭大运河,而贯通着南北的运河又连接着五大水系。所以,只要一处莲花开,便“处处飘散莲花的清香”“遍布翠生生的绿”了。只要一想到这舒畅喜悦的情景,作为诗人的商震便想起了那句千古名诗:“接天莲叶无穷碧”。
杨万里的这句诗确实诗意盛大,意境辽远。商震说:“好诗不是有好句子,是有‘接天’和‘无穷碧’的意境。”我十分认同。《当代·诗歌》正在“接天”和“无穷碧”,我深以为然的同时看到同仁们的努力,又颇觉欣慰。
从2019年开始阅读新诗并创作至今,我领会过新诗的苦难辉煌,也领略过诗意的盛大壮阔,更领教过新诗的虚幻高蹈、低俗下作和诗人的卑微渺小与蝇营狗苟。曾有一段时间,从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大刊物、选本的诗歌作品来看,当代诗歌给我的观感就是流水线上生产的复制品或赝品。千篇一律的生活,大同小异的情感,就连柔情蜜意和艰难苦恨的细节末枝也似曾相识。令我反胃到远离诗歌,直到最近读《当代·诗歌》,复又燃起阅读的兴趣。
我们将拥有一个又一个
打碎,又拼接的日子
我们将拥有神
以我们的肖像塑造
——(津渡《易碎的和完整的》第一节)
在草木相间的人世间,我们发现,不论是破碎的还是完整的,人们似乎都在以自己的需求塑造着我们的世界。此诗的语义不难理解,但我最想说的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是要说出我们“不能说出的部分”,而不是在“去主体化”的现代性表达上一路狂奔。
想象一下西山的通宵夜饮,
再想象一下你我顶着各自的月亮
我们一事无成,心中住着英雄
我们墨守成规,眼里杀人越货
页岩的山洞被酒缸占领
十年陈,二十年酱香
来,说说吧,洒家这厢有礼了
山里的人常常停下来,和群山谈一谈
这时候不需要声音
也不需要《道德经》
——(胡茗茗《我能说出的部分》节选)
老实说,我不能准确地说出胡茗茗能说出独属于她的隐秘的部分,但一句“我们一事无成,心中住着英雄”,实实在在地激发了我心底埋伏已久的情感。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可能不敢向世俗发起挑战,但我会坚守良知、保持初心的。我相信很多人也怀有这样的信念,绝不会甘心成为生活的附庸。我读过太多辞藻华美的诗句了,但那是没有真我的空洞的写作。虽然当代诗人写了很多、发表了远超唐诗宋词数量的诗歌作品,可能是基于某些考量,我感觉当代诗人的内心是封闭的,你读他的诗歌,并不能感同身受。就像胡茗茗在《到了这个年纪就透明了》书写的,“能救回来的真相实在是寥寥/太多世间的苦不能假设/我不瞳,你也深藏三千河流/继续读书、示弱/和这个年纪不由得泪眼婆娑”。说心里话,在底层谋生,我非常理解向社会妥协、向世俗低头、向社会示弱的与自己和解的生存哲学。但作为知识分子,如果就此甘心成为生活的依附者,我会低头无视地走过。
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曾说:“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这个社会的痛苦和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称作文学的。”看看我们今天发表在各大刊物上多如牛毛的诗歌作品,这样的被称为“大师”的“著名”的诗人的文学作品还少吗?“我来到这世上/四十多年/是不是黑暗中/也有一些什么巨响/我已经听不见了”(起子《万籁俱静》)。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我想,当代诗人是到了应该自觉摒弃低俗媚俗烂俗的小情调写作,打开心灵的窗户,倾听时代呼声和人民心声的时候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小时候读到这些诗句,我不知道杜甫、陆游、辛弃疾这样的诗人在他们那个时代经历了什么,但我的的确确被他们真心真意的诚挚情感所打动。现在,我也是写诗十余年的文学中年了,但当我回望我们每天所生产的海量的文学作品,我不知道几百年之后,人们能从这些文学作品中考证些什么,但我敢肯定,我们很多文学作品都没有“以诗为证”的东西。
我小时候以听话著称,老师教的,喇叭广播的
我都深信不疑。我相信贫穷是财富
苦难是磨炼,但自从看到一个老人饿昏在路边
我就开始憎恨、诅咒苦难和贫穷
像自从知道世界上有了鳄鱼我就不再相信眼泪
——(剑男《我怀疑》节选)
读到剑男的这首诗时,我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尤其是听到世界纷乱的枪炮声和哭泣声。我都不知道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了。但怀疑归怀疑,回到我们各自安放的心灵,回到我们的诗歌场域,我发现,新诗在“他们诗群”提出“pass北岛”与“诗到语言为止”的著名论断之后,尤其是从“第三代诗人运动”开启的诗歌解构主义浪潮,从而剔除了宏大的主体叙事和“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行吟与抒情传统,转变到个人化叙事和碎片化信息处理系统中心进行情绪化的渲染与低吟浅唱了。这种借鉴西方叙事原理的不言其义又不言自明的现代性书写范式,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创作理念和命名,但我认为“诗到语言为止”的现代性诗意书写,其实还是古典诗词欲说还休的艺术还魂,也就是说汉语新诗的现代性表达亦只是在语言和技法上生发的时代性嬗变。
写诗十余年,我读了很多现代诗,也借鉴尝试了很多现代诗的创作技法。但在阅读与创作的实践中,我发现现代汉语新诗在语言和技法上确实较“舶来”时圆润成熟了许多。但有一点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汉语诗人为何没有了为良知发声的勇气?为何丧失了为民族精神输血的冲劲和动力呢?对于现代进行汉语诗歌写作者的这种集体沉默,不管是有意识地集体转向,还是下意识地自我沉沦。这绝不是现代诗人才商和情商双重达标的高度体现,恰恰是当代诗人在社会主义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受“活在当下”思潮影响,从而表现出在乎个人前途命运,计较名利得失的结果使然。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养活一团春意思 撑起两根穷骨头。”老实说,我非常喜欢这样充满骨血气节的诗词。今天闲谈至此,我还想说诗歌精神和民族气节固然需要塑造与赓续,但诗人生在国家强盛的时代中,也是万幸。反过来思考当代诗人的圆滑和世故,其实也是诗人的幸运和福祉,毕竟国家幸比诗家幸更符合庶民的利益与期盼。
周敦颐赞美莲花的诗文虽然有知识分子把人格理想化的情感倾向,但如果就此认定世无“出污泥还不染”的人,则显得“局狭”。在商震看来,莲花是依赖淤泥的,只有“从淤泥中汲取养分,才能绽放得挻拔,就像诗人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不能把自己排除在芸芸众生之外。”我亦认同“躲在书斋里写诗,会缺少生活气息;吊着书袋子写作,不会有自己的感情流动。”我赞美莲叶和莲花,是赞美像莲叶和莲花一样的诗人与诗歌,作为诗人的商震在这时表现出了诗人的感性与浪漫。但作为编者的商震,我们又在这篇洋溢着诗人浪漫主义气息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他对《当代·诗歌》的热忱与抱负。读了《当代·诗歌》两期试刊,感觉这本杂志担得起当代诗歌的引领,对得起诗教的伟大传统。在卷首语里他还说《当代·诗歌》的作者都是芸芸众生,都在呈现现实生活,都在表达自己的感情。对此,我亦非常认同,因为从《当代·诗歌》中,我读出了当代诗歌的现代性和可能性。
从现代化进程的根本上来讲,我们的现代化,是从外部输入并先从沿海地区随着“改开”的春风逐步延伸到内地的。但是不管现代化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现代化的确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了。就诗歌写作而言,我们的现代性表达还未完成“东西”融合的本土叙事,但是《当代·诗歌》的努力方向,也是当代诗人的任务和使命。
有一段时期,一些人天天叫嚣着给反映打工人精神苦闷的“打工文学”更名,美其名曰“劳动者文学”或“新工人文学”等等。冀望通过这种粉饰苦难的命名方式来提升“打工文学”的精神质地,多少都显得有点滑稽和可笑。我实在想象不出,不能反映打工人粗粝生活和精神苦闷的底层叙事,还能称之为“打工文学”吗?如果当代诗歌离开现实的生活场景和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性,诗歌的现代性又如何表达?诗人的诗意抒写又如何反映时代?
最近闲来无事,偶尔刷到一些有关诗文的视频,非常直观,这里不妨试举两例体现现代性的视频文案。比如说我爱你,用古诗词表达就是:“入目无别人,四下皆是你。”如果你连一个倾诉的人都没有,用古文表达则是:“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就网络上的视频效果来看,白话文的现代性与古诗文的互译确实直观明了,高下立判,但要说新诗的现代性表达一无是处,也失之偏颇。
《当代·诗歌》在“开卷”“致敬”“中坚”“拔萃”“星河”等重点栏目里所刊发的诗歌作品虽然风格迵异、题材多样,凸显了当代诗歌的较高水准。关于当代诗歌的现代性书写,我想谈谈起点颇高的“处女地”。本期所刊发的四川籍青年诗人宁不远也写了一首很有现代性的诗歌。他在诗里写道:“古人 中国古人/我没见过他们说/我想你/他们只说/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我也没见过他们说/我爱你/那么他们/在爱情降临的时候/说什么呢”。(《古人》)从情感的表达上讲,古人的语言确实意境优美、含蓄委婉,读来朗朗上口,令人回味。现代诗在抒情上虽然过于直白,却也有浓郁的诗情,轻轻吟诵,也有情感喷薄而出之感。现代诗说透了说白了,会流于肤浅,但这种直来直去的情感表达,往往也能增强情感的浓烈程度。比如这首《山茶花》。
早上出门
往大路上走
看见路边开出一朵红山茶
停下来
看了三秒
傍晚回来
又看见这朵红山茶
这回看了十秒
离开的时候想
下回看一分钟吧
一分钟
才对得起它
——(《山茶花》)
什么是诗歌的现代性呢?这就是。表面上看诗歌的语言确实像韩东所提倡的“诗到语言为止”了,但你又能从这些戛然而止的诗歌语言里回味出诗人想要表达出来的又好像没有表达出来的情感一样。这首诗表现的情感可能还不直观,因为他倾诉的对象是一朵纯粹的山茶花,它好像并没有完成人的情感嫁接和转移。但我们仍能读出诗人所要传递出来的信息与情感。这就是诗歌欲说还休的语言艺术。而现代新诗对这种语言艺术的运用,意即汉语新诗的现代性表达,我们可以从下面这首诗中领略一二。
妈妈一个人
住在县城
昨晚小学同学铃铛说
她爸妈常在我家打麻将
深夜才回家
她还说
常在河滨公园看见
我妈和朋友们逛公园
这两天蓝花楹
开满了米易
听起来
只是听起来
妈妈并不孤单
——(《蓝花楹》)
这首诗看起来轻松自如、散漫拖沓,但他借“花的热闹”和“不缺朋友”的娱乐游玩,反衬出“妈妈一个人住在县城”的孤单与内心的寂寥。作为子女情感的投递对象,“蓝花楹”这个意象承接住了诗人浓烈的赤诚与热情。
在中国传统诗词的道统中,我们发现,不论诗歌的形态怎样“城头变幻大王旗”,其精神的实质皆重在用情与含蓄。现代汉语新诗的写作者们虽然陷在小情小调的诗意书写中无力自拔,但他们所渴慕的博尔赫斯也从不提及的“水到渠成”的创作追求,而毫不掩饰自己运用各种虚晃一枪的现代主义写作手法,则类似于古诗词欲说还休的含蓄蕴藉法。
宁不远这首短小精悍的《蓝花楹》,虽然摒弃了行吟诗人抒情的技法路数,但叙述中的情景范式以及现代诗散漫的语法语义,仍然不脱古典诗人的窠臼,有中国山水画留白的影子。可见现代诗人在意境上“接天”与“无穷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当代·诗歌》的同仁们已经迈出了坚实一步。
作品散见《文学自由谈》《文学报·新批评》《诗潮》《中国诗歌》《芳草·潮》《西北军事文学》《打工文学》等。诗歌入选《华语诗歌年鉴》《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2011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文学的光荣》《中国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等。曾获首届打工文学大赛三等奖(诗歌),第三届广西网络文学大赛二等奖(诗歌)。出版诗集《当我卑微无名时》等。曾与70后陈才锋、90后许立志被《南方日报》人物栏目作为三个年代的诗人代表予以报道。现栖居蒙自。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本站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